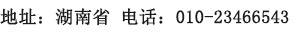第四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颁奖大会7月21日—24日在北京隆重举行,相关领导、专家和来自全国各地、香港地区及美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获奖作家出席大会。我市作家协会主席刘海军荣获一等奖并应邀参加了大会。
由中国诗歌学会、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国现代文学馆、人民日报社、北京大学、中国诗歌网等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会对参赛作品进行了定评,刘海军的作品《大洞记忆》,以较高文学水准在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,荣获第四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。
据悉,本届邀请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和港澳台地区及美国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、新西兰、加拿大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国家的位作家的作品,显示出大赛的国际性。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,并择优刊发于《中国散文网》。
中国散文网
中国散文网始是国内一个专业、权威、高端的公益性散文文学交流平台,已逐渐成长为国内第一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原创散文门户网。现有注册会员多万人,收录的原创文章累计逾亿字,更创造出日浏览量高达50万人次的记录。
中国散文网是一个以散文为主题的文章阅读网站,主要有经典美文欣赏、伤感日志、爱情散文等栏目,此外还增加了诗歌、杂文评论、短篇小说等相关版块。
散文鉴赏
大洞记忆
(广东·英德)刘海军
前些日子出差,驱车取道大洞至清新。车子从沙坝出发,先后途经龙潭、黄沙、社区、大田、黄塘,短短个把钟,就行走了大洞的五个村居。虽近深秋,沿途竹木茂盛,山清水秀,景色怡人。山风清清爽爽拂过脸庞,思绪和记忆一下子就被激活了,与其关联的点点滴滴填满心头。
大洞是英德的一个镇。如今英德有三个以“大”字开头的镇——大洞、大湾、大站。大洞的建制可上溯至明朝洪武二年。地名的来历与山形地势有关。从自然环境看,大部分属高丘陵地貌,自北向南从高到低延伸。街墟位于山间谷地一个幽深开阔的地方。“洞”的一个释义是“幽深开阔”。大洞是有历史文化底蕴的,康熙四十四年设浛洸属怀义都流陈图(今大洞、水边一带),道光十六年至民国时期设流陈乡。年10月,流陈乡分设大洞乡和水边乡。之后历经公社、区、乡的建制,年10月改为镇,沿用至今。
几百年来,大洞几乎成为偏处一隅的世外桃源。偏是说地理位置,整个镇域平方公里,离英德市区83公里,东接水边,南连黎溪和清新鱼坝,西通新洲,北邻沙坝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,与外镇通车的道路只有东出口的县道线。后来,随着双鱼潭水电站的建设,北出口麻蕉与沙坝的公路开通了。今年,西出口县道“大新”(大洞—清新禾云新洲)水泥公路全程通车,蜿蜒在高山深谷中,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,乡亲紧蹙的眉头犹如延伸的公路舒展开来。封闭已久的大洞总算接纳八面来风。听说,大洞人去清新买屋、赴墟的人比去英德的还要多数倍。
我对大洞的认识和了解由来已久。
一是姻缘。由于地缘相接山水相依,细数一下,我在大洞有很多亲戚。祖辈一代,我祖母的娘家在苦竹坪,那个村子毗邻天堂山,山高水远,林木茂盛。小时候,父母和伯父带着我们兄弟,翻山越岭,去那里探亲,单程要步行好几个时辰;父辈一代,我母亲的娘家在麻蕉大坑口,现在的双鱼潭电站上游。电站蓄水淹没了原来的家园,我的老舅们、老表们都已搬迁至大洞墟镇,原大洞粮所一带,几乎成了“长引一条街”,那里的新居民,我的亲亲戚戚占了七七八八,当然,探亲也方便得多咯。我母亲还有一门干亲,在麻蕉大木青村,小时候常常去探亲,那里的亲人种香瓜西瓜甘蔗,诱惑力很大。我的大伯母,从大洞的黄沙嫁来沙坝。到了我辈,三个堂姐成了大洞媳妇,阿凤姐嫁至陈洞,水娣姐嫁去过江富,观娣姐嫁到大社。而我的二嫂则从庙坑远嫁到沙坝。在那交通靠走的年代,山重水复,人地两生,冥冥中,深谙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。
二是山缘。住山靠山。从祖辈算起,我们在沙坝与大洞接壤的深山老林,砍野笋,种木耳,烧木炭,做木材,放野牛,来来往往与大洞有很多交集,年长日久,焉能不熟!
二是商缘。我祖辈父辈织箩手艺的名气在大洞可以说鼎鼎有名,我父辈住的老村子在沙坝与大洞交界的一个叫五指山的深山大窝,“五指山箩”的品牌口口相传经久不衰。我的祖辈依靠一手过硬的刀篾功夫,从选材、工艺、质量、价格等方面,在大洞、水边、西牛浛洸一带久负盛名,特别是在大洞,他们织制的“两耳箩”(一种可以穿绳子、又有两个把手的竹箩),因好用耐用,一直是大洞市场同类产品的佼佼者和抢手货。小时候,每逢大洞墟日,便由父亲带着,挑箩徒步到大洞墟镇去买。通常,提前一天,父亲就开始准备工作至深夜,依照年纪、身高、力气等综合实力给我们兄弟几个分好工,谁谁谁多少担都明确得一清二楚。我清晰记得,全是山路,道路又小又窄,上上下下,高高低低,蜿蜿蜒蜒,挑的箩体积大很占空间,不掌握技巧,难免碰碰磕磕羁羁绊绊。一趟下来往往要耗费三四个钟头。尽管这是一项苦差事,我们都很听话,按照分工,从没掉过链子。其实,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严重匮乏的年代,去大洞卖箩的过程,也是苦中有乐的,一来可以赴墟(赶集),长长见识;二来可以改善伙食,跟着大人饱餐一顿肥肉米饭;三来可以看场电影,分享声光艺术带来的喜怒哀乐。年届知天命,我很怀念那一段苦乐相伴、亲情相依的清贫日子。只是,在传统农耕时代传承了数百年的祖辈织箩手艺,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延伸渗透,而变得日渐式微,慢慢淡出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,更严重的是,作为物质或非物质的文化,濒临消失消亡。想想都不是滋味,心头涌起无限惆怅。
大哥说,上个世纪七、八十年,他曾和父亲长途跋涉去新洲卖笋干,一个来回两头见黑。尽管货重压肩,大哥的衣袋里装着一台称得上奢侈品的收音机,分享着空中电波带来的无尽乐趣。
我记得,三四十年前,大洞乡亲扛杉树到沙坝楼角村交易的场景。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在土名叫七八坑、佛子坳等山路上,晴日也好,雨天也好,扛树人络绎不绝,用或建壮、或羸弱的肩膀挑起一家人的生活和希望。扛树大军中,不乏亲亲戚戚。心地善良热情好客的母亲,经常煲一大文鼎的稀饭,让到来歇脚的亲人既可充饥又可解渴。
大洞人喜爱吃擂茶粥是出了名的。我猜想,这可能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无关系。远古时候,大洞人居住区域多属崇山峻岭,瘴疠流行。如何在自然条件下得到生存和发展?聪明的大洞人自然就会想方设法采取种种防范和治疗措施。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,他们的祖先找到了药食同源的方子——擂茶粥,一种有御瘴去疠药理功效的食品。此饮食风俗习惯沿袭至今。多年前,我曾写了一篇关于擂茶粥的文章,介绍了擂茶粥的制作工艺,讲述了相关的故事传说,在《清远日报》刊出,引起高度